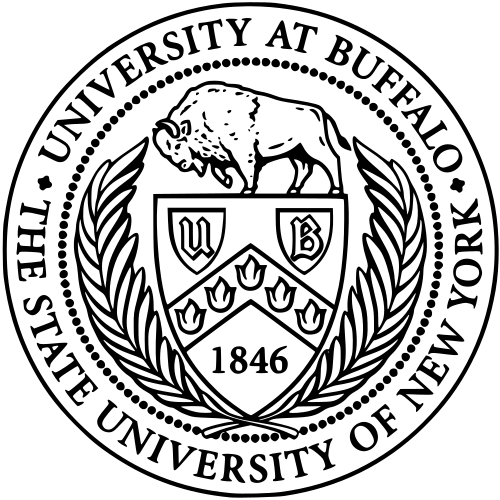悉尼节目回顾:科克托的《人的声音》
让人举步维艰的科克托于1930年创作的独角戏《人的声音》,在戏剧上加入了一半对话的元素,观众只听到了谈话的一半,写作风格坚毅,由朱利安·默费特所述。
观点:一个未经具名的女人独自一人在公寓里,与她爱着但却背弃她的男人进行一场愈加恐慌的电话对话。她原本坚定的态度逐渐在一个小时内崩溃,内心的绝望也逐渐吞噬了她。
目前正在悉尼节的Carriageworks剧场上热映的这部独角戏《人的声音》足够夸张,但由于观众只听到了对话的一半,使得戏剧变得更加坚韧。
这种对戏剧性氧气的剥夺意味着我们既同情主角的心理窒息,也对此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
独角戏有其要求。在最好的情况下,如同塞缪尔·贝克特的《克拉普的最后一卷磁带》和《不是我》,或者安东·契诃夫的《烟草的有害影响》,它们将观众置身于一个充满密闭情感空间的氛围中。
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们会打破我们与戏剧的时间荣誉协议,简单地留在舞台上过久。
科克托的戏剧情况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20年代电话的快速普及。
这个新的不人性的工具现在成为了“人的声音”的主要传达者 —— 丰富而悦耳的“灵魂”声音被分解为电子信号,以光速而非声音速度传输 —— 亲密关系的实质已被篡夺。
这种一夜之间的取代导致了不寻常的影响:距离被抹杀,声音被从身体中分离出来,一种被感知的幽灵性吞并了另一方。在科克托的戏剧中,女主角提到电话线中的声音如同死者的声音;对话者无形的幽灵用卷曲的线绞住她的脖子。
在各种方面,这部戏剧的世界已不再是我们所熟知的。
她应该退还的装满手写信的袋子;引发他们爱情的电报;使他们联系的电话交换机;以及充满其他声音的共享电话线 —— 这个世界已经灭亡。如今不仅电话普及且已数字化,而且整个通讯网络也发生了无法辨认的变化。
这就是将这部作品设定在今年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决定。
在Toneelgroep Amsterdam独特的舞台上,关键道具——电话听筒是无线的(这使得关于她脖子上的线的伟大台词没有意义)。女主人在iPod上播放着毫无意义的流行音乐。她的阿迪达斯运动裤和缺乏品味的迪士尼上衣暗示了一种衰老的当代“女孩女人”。

这些结构性的错误违背了所表演的原材料:电话线上的众声;一次联系的宝贵罕见;电话作为唯一而不稳固的跨大城市联系方式的感觉。脸书可能会拯救这个女人脱离她的命运。团体称其为“永恒”的这部作品只是关于它最公式化和陈词滥调的东西;其中令人痛苦的是它在历史上的定位。
更甚的是,导演伊沃·凡·何夫要求演员哈里娜·瑞因采取的表演风格明显偏离了戏剧本身。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高能量、心理驱动、喘不过气的自然主义;瑞因是一个充满各种陈腐行为的真正的人类喷泉 —— 从公交车上经常听到的那种。就这一点而言,这是对一个80岁老作品有多少“现实主义”可读性的一次精湛展示。但关于科克托的剧本中并没有这样的暗示,它包含了他标志性的冷漠风格,他超现实的抽象美学形式。形式并非陈词滥调。科克托的女性是对女性的纯抽象;但这种表演把抽象物转化成了一种易于接受的电视式真实风格。
另一个令人反感的导演决定是将舞台设置成一个打破电话通话单调的设备。
在关键时刻,她离开电话直接向我们呼吁,也呼唤着她的恋人,如同邻居一样 —— 窗外的后窗式。这必须算是审美上的失败,因为脚本明确规定他们之间有整个城市。这使得这个困难的电话对话充满了戏剧紧迫性。
音乐,由几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和一首真正糟糕的悲凉法国主题曲组成,不时地穿插播放,并在前景中持续几分钟,既糟糕又不与戏剧融合 —— 保罗·西蒙的《离开你的情人的50种方法》,比如说,是使她自杀的无聊曲子。
在这些限制和失败中,所有这些都属于导演的责任,而瑞因本人依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存在。
只有在极少数时候,我们才会从她的请求中慢慢转移注意力,承认她所展示给我们的心理可信度。大多数情况下,她促使我们要全神贯注于她每一个咯咯笑声、哼声和抽泣声。甚至当她亲吻男人的空鞋子时,这一令人遗憾的时刻也因她带来的优雅和真诚感而变得能够接受。
Julian Murphet是一位现代电影和文学教授,也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现代主义研究中心的主任。
这篇评论最初发表在The Conversation上。